萌发于19世纪中期的现代主义运动是对传统审美的全面反叛,小说、绘画、诗歌、戏剧、音乐、舞蹈、建筑、设计、电影,几乎所有艺术形式皆在这场运动中被彻底颠覆。近两百年来,现代主义余韵未消,当年的文化先锋们仍深刻影响着我们今日的文化生活。在这本关于现代主义的百科全书式著作中,彼得·盖伊将“现代主义”这个看似抽象的概念具象化为一个个现代主义风格代表人物或一件件名垂艺术史的经典作品,他以波德莱尔为这一波澜壮阔的研究揭开序幕,追溯了现代主义最初如何以革命者的姿态出现于巴黎。随后,马尔克斯的小说、毕加索的绘画、斯特拉文斯基的音乐、盖瑞的建筑等轮番出场,盖伊在书中将它们或相互比较,或相互融汇,以博学且风趣的笔触为读者呈现了一场异彩纷呈的盛会,而现代主义发展、壮大直至衰退的过程在其中得以清晰的显现。
彼得·盖伊(1923—2015)一生著有超过25本著作,《伏尔泰的政治》《启蒙时代》《魏玛文化》《布尔乔亚经验》等等作品奠定了他在同时代历史学者中的重要地位。他的研究主题涉及中产阶级、启蒙运动等诸多社会文化史领域,其中,现代主义是他长久以来一直充满浓厚兴趣的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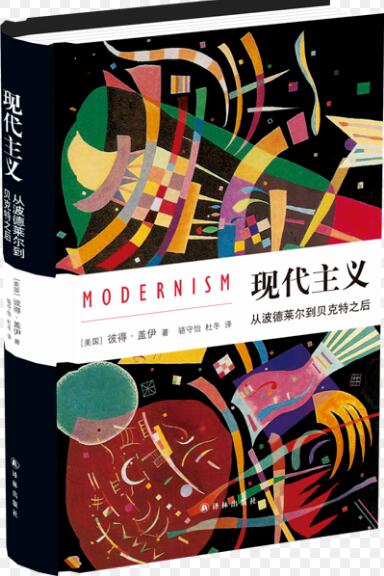
《现代主义:从波德莱尔到贝克特之后》
[美]彼得·盖伊 著 骆守怡 杜冬 译
2017年2月
一
德国现代主义艺术家和作家曾在戏剧、小说、诗歌、绘画和建筑艺术上有过杰出的贡献。而希特勒的上台就给他们敲了丧钟。当希特勒于1933年1月30日被推举为德国的总理后,他所信任的那伙人以惊人的速度和可怕的效率施展了新获得的权力。全德国上下,对政治反对派拳脚相向的事件,无论是其数量还是狠毒程度都与日俱增,他们甚至袭击国民议会中的社会党议员,而这些人一般公认是可以免遭攻击的。国家却对此冷眼旁观,不为所动,甚至还幸灾乐祸。“席卷德国的这种变革,其发展之迅猛,在当代看来是令人震惊的,即便在历史中,也颇为罕见。”眼光深远的希特勒传记作家伊恩·克肖如此总结当时德国人的普遍心态和纳粹党得逞时的力量。“这种局面,是貌似合法的手段、恐怖、操纵,还有心甘情愿的合作共同造成的,不到一个月,魏玛宪法所保护的公民权利就被一扫而空。两个月之内,随着最活跃的反对派政治家锒铛下狱或逃亡海外,国民议会向强权低头,让希特勒控制了立法机关。四个月之内,曾经权倾朝野的工会也被解散。六个月刚过,所有的反对党或举手投降,或心甘情愿地被人解散。”早在1933年3月,新的当权者就公开宣布要设立一个集中营,这第一个集中营就在慕尼黑附近的达豪。无论是高雅文化还是低层文化,不管是公司老总还是保龄球俱乐部,是编辑或足球队,都要在绝对的控制之下,这个政策长驱直入,所遇抵抗甚微,人们纷纷赞成。突然之间,未经一战,德国的现代主义者就发现自己以及大胆的艺术创新已经被永久地、不屑一顾地宣布为“undeutsch”,即“不属于德国”。
国家社会主义党政权对现代主义的第一次打击,不过是其反犹主义的顺带之举。由于国民议会已经变得无能为力,在立法机关又大开绿灯,要“清洗”德国社会,因此纳粹迫不及待地将自己传授已久的反犹美梦变成现实。犹太人被全面肃清了:无论是犹太公务员,还是犹太乐队指挥和剧场经理,犹太教授(虽然人数不多,但是在魏玛共和国时期比起德意志帝国来多了不少)、犹太记者、犹太演员、犹太画家和作家,很快他们就遭到解雇,并且无人来雇。
当然,这些被剥夺了生活来源,并且往往被驱逐出祖国的德国犹太人不可能都是现代主义者,甚至其中现代主义者的比例也不算特别高。解雇犹太人的高潮其实是经过精心选择的:只要是个犹太人,在纯德国的才智之士中间,就会被视为讨厌的外人。尽管犹太人莫名被扣上 “Kulturbolschewismus”(文化上的布尔什维克主义)这顶帽子,德国的大部分犹太人对“文化上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却都毫无好感。他们和德国大多数非犹太人一样,喜欢的是大众品位。1937年纳粹开始他们精心组织的巡回展览,将那些所谓“堕落艺术”示众之时,其组织者发现,在112位因其作品所谓“堕落”而被选中遭人耻笑的画家中,只有六位犹太人。可是文化上保守的犹太人,依然逃不脱国家种族排外方案的罗网。比如著名的古典音乐指挥家布鲁诺·瓦尔特,他的专长本是莫扎特的歌剧和马勒的交响乐,却不得不在1933年春天逃往奥地利,因为有人威胁他如若胆敢继续在德国的土地上指挥乐曲,则会遭到暴力驱逐。还有顶尖的学者,诸如新康德主义哲学家恩斯特·卡雷西尔以及艺术史学家埃尔温·帕诺夫斯基,两人都和现代主义艺术和文学本不相干,可因为是犹太人,结果都被解除了教授之职,不得不在国外另谋出路,结果和很多其他人一样,他们都去了美国。
但有些被迫流亡的人则是彻头彻尾的现代主义者。仅仅因为是犹太人就被开除的个案中,可能最有名的就是那位善于创造、无所不精的柏林德国剧院导演马克斯·赖因哈特。这个精明的剧团经理上演戏剧时,不管该剧的起源如何古老,都能让现代观众看得欲罢不能。他接过德国、法国和希腊的古典作品,给哈姆雷特穿上现代服装,又在一个旋转的舞台上上演《仲夏夜之梦》。他得到的奖赏就是被迫逃亡美国,在那里继续进行惊人的、极有创意的设计,只不过规模大不如前。

柏林德国剧院导演马克斯·赖因哈特被迫逃亡美国
也不是所有流亡海外的都是犹太人。贝托尔特·布莱希特是魏玛共和国最有创意的剧作家,他早期信奉表现主义,然后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启蒙主义。1933年2月28日布莱希特离开了纳粹德国,这时距离柏林国会大厦纵火案仅过去了一天,与此同时,布莱希特近期的剧作也在德国各邦遭遇了最猛烈的排斥。在这一触即发的情势下,布莱希特估计他很有可能会被逮捕,之后肯定会被折磨,于是他逃亡海外。
纳粹党对德国先锋艺术家零散任意地攻击,很快便集中火力到准确选定的目标上。1933年5月10日发生了臭名昭著的焚书事件,这次恶劣的行动说明尽管纳粹党恶贯满盈,却依然得到了广泛的支持。受到指责而遭焚毁的这些书,不仅包括犹太作家的作品,也包括诸如海因里希兄弟和托马斯·曼等雅利安作家的著作,这是政治化的、粗俗的条顿主义怒火的喧嚣。这次焚书是一次情感的爆发,针对的是某些事件和想法的回忆,例如让霍亨佐伦帝国寿终正寝的1918年11月革命之“耻辱”,和自由主义、陈年旧账(语出艾略特)等凡此种种彻底告别。当时对焚书一事的宣传,仿佛是兴高采烈地给现代主义下葬。一个世纪之前,伟大的德国诗人海因里希·海涅曾说过,如果某个国度里有人焚书,则他们必会焚烧活人。只不过当时几乎无人记起这话,日后许多人才会想起。
这场针对“非德国精神”的运动,在柏林焚烧了约两万本书,在德国其他城市则稍逊一筹。德国学生组织早在4月间便积极准备这场运动,打算在全国各地,包括大学里到处张贴十二篇杀气腾腾的文章,以此比纳粹自己的学生联合会更胜一筹。第七号文章如此写道:“如果犹太人用德文写作,那所写的必然是谎言。从今以后,犹太人若想出版书,就应当强制他在书上用德文注明:‘从希伯来语译为德语’。”这套大话中公然的谎言的确是后无来者,让人望尘莫及。但其后的焚书运动得到了学者和学生们的全力支持,甚至还有消防员被派遣过来以确保火势不失去控制。不仅仅是那些和魏玛共和国作对的顽固反动派欢迎将这些“非德国”的作品一举捣毁,甚至另类的抒情诗诗人如格特弗里德·贝恩和有名的哲学家如马丁·海德格尔也公开赞成纳粹政府的做法,还帮助压制了一股重要的反对派。学者只能勇敢刚毅,一心爱国,种族纯净,和人民也就是大众站在一起,对世界主义、理性主义和其他启蒙理念则应不屑一顾,这是纳粹党政权所支持并许可的唯一方式。
二
这样的举动是否属于反现代的现代主义?纳粹政权如此行事,主要是展望未来,还是回归历史?希特勒的千年帝国土崩瓦解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但这些问题依然没有答案,也不会轻易得出答案,因为纳粹的理念和行为都有多方面的诉求。另一方面,纳粹重视技术,让技术忠实地为自己服务,他们赞赏诸如汽车和飞机这一类现代发明,并大张旗鼓地将其运用到备战之中。从1933年开始,他们就巧妙地重整德国的武备,并积极地将德国的工业纳入到为即将到来的战争服务的轨道上来。
纳粹将当时新发明的设备无线电出色地运用于宣传攻势,也表现出该党重视现代化的一面。纳粹画家们发现有一个场景大受欢迎,这就是描绘一个德国乡村家庭聚集在一台简单的广播旁,专心听广播,标题是“Der Fhrer Spricht”——元首在讲话。支撑这种现实的现代化措施的是纳粹党乌托邦式的政治理念,即幻想出一个由新人类统治的新世界,一个没有犹太人的雅利安人世界,纳粹朝着这个伟大的变革努力,做得坚决彻底——这就是那些信奉德国民族性格的人所称道的德国人的“一丝不苟”(Grndlichkeit)——没有留下一点余地,他们正是如此将那些对德国文化遗产有重要贡献的犹太人塑造成为社会寄生虫。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期,柏林和外地大学预科学生们拿到的音乐歌本上,将一首脍炙人口、无法禁止的歌曲《罗蕾莱》(Die Lorelei)的歌词作者写为“佚名”,可实际上,正是海涅这位受过洗礼的犹太人在一个世纪前书写了这段不朽的文字。
可另一方面,新时代男人和女人的理念又奇妙地带来了陈腐的风气。理想中新人类的形象为德国女人规定了英雄的、自我牺牲的角色:Kche,Kirche,Kinder,即只能围绕着厨房、教堂和孩子生活。在这个死板的社会中,尽管有盖世太保时时监控,还有市民迫不及待地报告自己的邻居对元首不够忠心,却依然有几个政治笑话流传于世,其中一个就是关于纳粹党人所梦想的新人类究竟是什么模样:和希特勒一样金发碧眼,和戈培尔一样身强力壮,和戈林一样苗条颀长。认真说起来,哪怕没几个德国人能达到这个彻底洗心革面的高标准,但他们还是可以仰仗希特勒的光环,让自己知道元首在带领他们,元首为他人操劳,为他人受难,为他人指明道路——他就是救世主耶稣。
对希特勒的崇拜中,有些因素是长存不去的,有史以来就时常出现这样的现象:人们自甘臣服。纳粹的头目所认可的所谓日耳曼人的理想——即新人类的理念——不过是七拼八凑的大杂烩,其中包括民间故事、文学创作,还有对古往今来的历史传说的添油加醋。真实的历史根本不可能击败这条顿式的梦幻。在纳粹思想的所有自相矛盾之中,最重要的就是官方意识形态中的厚古薄今,而他们所追思之古代,最起码也被当代重新粉饰过。
三
纵然对历史百般涂抹,德国的现代主义却未能因此得救。纳粹当政第一年,就设立了一个无所不包的帝国文化处,在其麾下各部门网罗了有才能的作家、出版社、剧院、广播、音乐,种种艺术都在宣传部的庇护之下,也就是说受戈培尔的领导,戈培尔受命执行希特勒明确的文化方针。元首早在1933年2月就曾说过:“我们要把真正的德国文明、德国艺术、德国建筑、德国音乐,还给我们的人民,这将重建我们的灵魂。”希特勒醉心于苗条、真实、金发碧眼的裸体,还是理查德·瓦格纳的崇拜者,因此对于德国表现主义的油画、制图、诗歌自然就无甚好感了,哪怕这些大胆的艺术创作大都来自德国当代非犹太人的艺术家。因此,德国的现代主义者或逃亡海外,或沉寂无声。
纳粹党不需要文化上的现代主义,最明确的证据是1937年7月举办的一场耸人听闻的展览,最早在慕尼黑展出,然后又在德国另外十三个城市展出,这就是Entartete Kunst——即所谓“堕落艺术”。在展览挤挤挨挨的墙壁上,或是目录里,人们会发现,现代艺术作品被巧妙地安排,和精神病院常年疯子的画作并列展出,以强调现代艺术画作的幼稚、病态甚至是疯狂,指出其是如何强行混入了消极的、忍气吞声的德国艺术之中。可是仅在慕尼黑一地就有两百万人参观了这场展览,在其余各地也有一百万人,这个统计数据与其说纳粹的宣传得逞,倒不如说观众对这些从德国各博物馆里全部充公的现代艺术作品是如此神往。最后,这些画作有些在柏林消防总局被付之一炬,有些则被私人收藏,或以高价售往海外。
精心策划的丑化现代艺术的运动,自身的矛盾也有增无减。有些纳粹党的要人按官方的要求对自家的祖先进行调查,却惊恐地发现,他们绝不是纯种雅利安人,有犹太裔祖父母。德国艺术家中某些最狂热的纳粹党人也惊恐地发现,由于偏好的现代主义,他们被正在崛起成形的纯雅利安艺术排斥在外。在这悲喜剧的失落例子中,最有戏剧性的可能莫过于埃米尔·诺尔德。作为堕落艺术的样本陈列的画作中,有26幅是诺尔德的作品,有他奔放的油画作品,异国风情的木刻和精美的水彩画,颜色夸张,形体扭曲,线条粗犷。他曾周游各地,后来在北德一个偏远的小村里隐居度过大半的创造生涯。他创造的主题从花卉和异域风景到情感激烈的基督教场景,而这一切,如他所说,都是致力于描绘“深邃的精神,宗教和微妙之情”。

画家诺尔德作品。他曾是纳粹党党员,但仍然遭到残酷对待
多年以来诺尔德都是一个老派的、闭门不出的先锋艺术家,但他很早就是自己所在的石勒苏毅格——荷尔斯泰因地区纳粹党的党员,并热情地接受了纳粹的世界观。而后,他就遭到了残酷的污蔑。到1937年从各博物馆没收的他的油画、素描和出版物据记录为1052份,其中大部分遭到摧毁,这在所有德国“堕落”艺术家中是最多的。到了1941年,政府正式禁止他创作,不过他在自己偏远的乡村农舍里不声不响地违命而行,当时其他的表现主义者,如卡尔·施密特·罗特卢夫也被监察,被勒令退出艺界。还有一位现代主义艺术家,画家和雕塑家奥托·弗伦德里希则于1943年3月死于纳粹设在梅德纳克的死亡营,不过不是因为他的艺术风格,而是因为他的“种族”。
研究纳粹文化的历史学家曾多年争论一个问题:尽管1933至1945年统治德国的纳粹使艺术从属于政治,但同时也美化了政治。那个时代,形象和实质两相竞争。数千身穿制服的市民,整齐肃立如林,所有人专注热忱,僵硬地举起有纳粹十字标志的旗帜,令人炫目的灯光巧妙地互相交错,还有那激动人心的一幕:元首从阴影中走上前来,开始他那种长达两小时的讲话。展现纳粹公众建筑设计(通常也包括建筑施工)的宏大新古典主义风格,在人民中巧妙营造的神秘氛围,还有两部由莱妮·里芬斯塔尔执导的电影杰作:诱人而又臭名昭著的1934年纳粹纽伦堡党代会宣传电影,以及1936年柏林奥运会的电影。这些都是统治德国的纳粹党计划中的内容,就是要激起民众参与举国孤注一掷的狂热和自我欺骗的热情。

工作中的里芬斯塔尔
现代主义中的核心原则是自由主义,即无论对抗的是怎样的权威命令,也要解放人的本能和独创力。无论希特勒政权发现哪些现代主义的技术可以利用,自由主义已经在纳粹倒行逆施的革命中丧失了,里芬斯塔尔的电影就是个极好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