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演讲封面PPT
“从本质上说,地下组织是一个松散的集合体,它将年轻人的欢乐、艺术生产、主流的反抗和仪式等概念结合在一起。表演——是一个集体创作作品(McRobbie 2016) ,表达了青年文化背景下的日常美学,也是一种另类的城市世界主义……“艺术世界”的定义最初是由贝克尔构想、发展和推广的,它非常清楚地意味着艺术创作是一种集体努力的概念,从而将支持艺术作品的各种互补活动、收到的反馈、与公众的接触以及其他人的理解提上了桌面。合作在这方面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在我们所知道的所有艺术中,就像在其他人类活动中一样,合作始终存在”(贝克尔1982:7)。这种合作不仅发生在同一个空间或时间框架内,而且延伸到艺术品的整个生产周期,从构思所需的材料到分发和认可所需的资源。为了使所有这一切走到一起,必须有“一群人的活动是必要的作品生产的世界,也许其他人,承认为艺术”(贝克尔1982:34)。艺术生产所涉及的合作性工作意味着关于行动者合作方式的约定的存在。这可以在朋克领域看到: 当个人合作时,为乐队、唱片公司、巡演等的发展建立了必要的约定(Guerra 2013a,b; Maanen 2010)。贝克尔强调了这些非正式协议对于分享特定环境的知识的重要性,并指导如何找到这些知识。这与在艺术层面上所发现的联系类型密切相关。在艺术的运作过程中,艺术既决定了一般的社会规则/习俗,也决定了艺术世界更为具体的运作方式。蓬勃发展的朋克音乐是由业余和专业的年轻音乐家以及非常忠诚的,虽然规模不大的听众所组成的。”
今天我要分享一个研究很久的话题,就是关于中国朋克,它是一个从地下的原真性到平台视角研究的极好案例。首先,我要反思这个议题是如何与世界主义相联系的。我认为我的朋克研究和朋克实践本身就是一个透视的过程。从表面上看,我觉得朋克话题初听上去很有趣。人们也觉得它被讨论挺多了,但实际上的研究过程带给了我复杂的感受。例如,当我去不同的学术会议谈论我从事的研究时,大家经常说,这是一个令人着迷的话题,会说我是朋克,或者我曾经是朋克。于是通常能很快地进入这个话题,这时常让我觉得朋克挺“地上”的。这一带有世界主义色彩的举动时常能引发许多对话与交流。今天我想谈的是朋克这种从“地下”到平台化,网络化的转变,这同时还折射出一个更大的议题,就是“地下”是否已经完成了向“主流”的动态转变,它还是独立于一切的存在么?
我不是一个朋克,朋克歌曲带将我领入朋克研究的大门,从一个研究者的角度,我进行半朋克式的而非完全的实践,由此我不会从非常理论的角度来谈论朋克研究。我先介绍一下朋克研究的谱系,看看这些有趣的流行议题的研究成果。诚然,朋克研究已经从纯英国式的西方角度扩展到更多的领域,并且有着清晰与强烈的意图。从下面三本书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点。

朋克研究谱系
第一本书是Dick Hebdige写的《亚文化:风格的意义》,这是关于英国朋克的一本非常经典的书。虽然它遭受了诸多批评,但它仍然与后亚文化时代息息相关。在朋克研究高峰时期的古典时代,它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力,在这里我就不展开了,直接进入现在被广泛应用的另外两本书。
第二本叫作《阅读朋克:从本地化到全球化的研究转向》,接下来的这本是《朋克的全球化突袭》。他们实际上是体现朋克组织者意图的系列书籍。这些书的作者和编辑刚刚进入朋克场域的时候发现以前的研究者只聚焦于西方朋克音乐场景,由此他们涵盖了许多帕金森患者案例以及其他的社会背景。例如巴西和西班牙这些通常被视作“南方”地区的学者,对我关于中国朋克的学术化研究方法很感兴趣。从我们刚刚介绍的第一本亚文化的书你也能看到国际学者还是对于非西方的朋克场景非常陌生,然后在第二本书里能看到一些更为反思的材料,对于公共话语多了更多的思考。

Pandemics的相关介绍
从这张图上你能看到朋克、研究与网络的谱系,特别是关于Pandemics。这本书非常有趣,它解释了朋克研究为何变得如此活跃,是因为曾经的老朋克现在成了不同的大学里的教授,使得他们对朋克场景本身有了发言权,朋克研究也因此成为了一个充满活力的研究场景。另一个我想谈的是King Smith会议。这是一个基于城市的国际文化、艺术与学术活动。这个活动吸引人的地方在于它结合了学术性的讲座和讨论,也有许多朋克演出现场。我觉得目前的学术会议组织是一个挑战,它告诉我们“地下”的场景如何变得既学术又实用。
现在我来转向中国朋克研究的阐释。在2011年,David Odell描述过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朋克的场景,它们来自Lewisburg和他处的印象。直到2017年,他们已经持续观察20年了,在中国关于朋克的展览倒没有那么长的历史,我们仍然可以从中看到许多抵抗的实践,不过在我看来,这是一种对朋克政治的理解和妄想。因为朋克音乐人开始停止对西方革命药方的意识形态的寻求,这使得我与西方学者讨论中国朋克实践的相关疑问。
时间在推进,技术在进步。似乎带有原罪的平台开始将朋克音乐人裹挟其中。我说的朋克音乐人群体尽管没有进行非常明确的关于政治的抵制性实践,但他们依然做了非常多隐性尝试。例如这张图传达出来的有趣的信息。像他们把作品放在网易云这样的平台上时,他们觉得在平台上进行批判既隐蔽又有趣,这就是一种抵抗行为。下面我想谈谈自己的书里关于朋克的具有协作与多维特点的叙事。
如前所述,当人们开始谈论朋克的时候,它常常被收入一些关于摇滚乐或嘻哈音乐的书中,而不是单纯的讲朋克的作品。由此我认为进行朋克研究是一个非常独立的主题,这就是我下决心进行深访的原因。我对朋克的研究可以回溯到2013年,直至2017年,我已经采访了非常多朋克音乐人与朋克粉丝,也让自己持续处于鲜活的一线。与此同时,之所以说它具有协作的特点,是因为这本书有来自葡萄牙与英国的学者参与,他们关注于朋克歌曲中的捐赠状况。从撰写这本书的过程来看成,我觉得这是一次密度极大的谈话过程。我们采用了一种与西方意识形态非常不同的视角来谈论朋克,大家真正地开始关注非西方的朋克场景,并试图专门为此搭建网络。
从地下到全球的网络
在看着“地面”、“地上”、“地下”这些概念时,我开始思考,“地下”永远不会仅仅是一个概念。它为我们带来了许许多多的东西,其中有一样我觉得是与地域有关的传统。由此我试着把沈阳的地下音乐场景放到一个更大的视野中去审视,一位沈阳的音乐人说东北和内陆出现了挺长的一段孤立的时期,并回溯了北京和该地的音乐合作史。长期在一个有限的,隔绝的区域里的自我交流,让这里的地下音乐场景成了一种自我管理与自组织网络化的现象。

《生命文献——沈阳地下音乐1995-2002》展览相关信息
与自我管理和自组织网络化相伴的也有其独特之处。例如朋克现场或摇滚现场的出现通常都离不开商业化的酒吧,小型的沙龙或者是高等学术机构里。这些半真空的文化空间逐渐转化为沈阳的地下音乐场景,有时当代艺术成分也参与进来。所以说如果这种地下的场景着实带来了什么难题的话,可能就是它过于真实地反映了我们传统的变迁,折射出背后丰富的历史图景。我还想分享一个关于中国地下朋克网络的例子。你可以在这张图上看到一个面馆,它是由朋克音乐人开的,也是我重要采访对象之一。这个面馆和市面上的其他餐馆完全不同,不仅是看起来非常像一个地下的场景,而且里面的音乐人和厨师都有纹身,他们表现得非常朋克。比如,他们会告诉顾客,如果你不想到这儿来就不要来,这是极为朋克的态度。

演讲中提到的餐馆
从这个角度看,当人们开始关注这个空间和这家餐厅时,会觉得它是一个极为非主流的场所,而事实上它也成为朋克音乐人自己的一种非常独立的联结网络。正如我强调的那样,朋克不仅仅关乎地下,同样也是在全球的网络中显示出在空间和社会语境等维度里的独立性。音乐原真、独立的特性可以一种甚至不依赖于地下摇滚乐形态存的自成体系的朋克实验音乐与电子音乐。这种自成体系的朋克沟通网络可以直接与全球范围内的独立音乐网络联结,并且在手工制作(如DIY)等方面取得很大的成绩。
而从具体的朋克个体身上也可以看到这一点,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解释。首先,Odell在朋克场景中引入了一些混合的标签,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朋克群体、乐曲和场景很显然极大地受到了西方趣味的影响。而第一代早期的中国朋克音乐人也是从系统化的互联网络、非正式的社交网络与编曲工具中获益,让他们的创作理念、乐队风格得以实现,这与我们在印尼看到的世界主义、都市主义的成形过程类似。然后我想在一个新的社会背景下为朋克场景添加一些额外的方面,因为在我们谈论朋克研究者如何研究之前,他们开始更多地挖掘非西方朋克研究的社会背景,但随后出现了一场新的竞赛,平台化语境开始出现,它也影响了中国和全世界的亚文化事物,尤其是在中国。
平台的网络化形构
在我谈论朋克研究者如何从不同的社会语境中挖掘更深刻的非西方研究视角之前,我想就朋克场域的新兴社会语境添加一些视角。比如大量平台式的话语开始出现并竞争,这深刻地影响了全球的亚文化事物的形塑,尤其是在中国。
接下来我会分享一档关于《乐队的夏天》的节目。这是一档聚集了许多老牌摇滚乐队的综艺娱乐节目,通常这些乐队不是曾经很出名但近年被遗忘了就是尽管目前很活跃,但还不是特别出名。由此我们可以说,《乐队的夏天》的组织或宣传是将朋克的场域从非常小众的群体扩展到庞大的粉丝基数群体,同时创造了一种远超其本身载体的亚文化景观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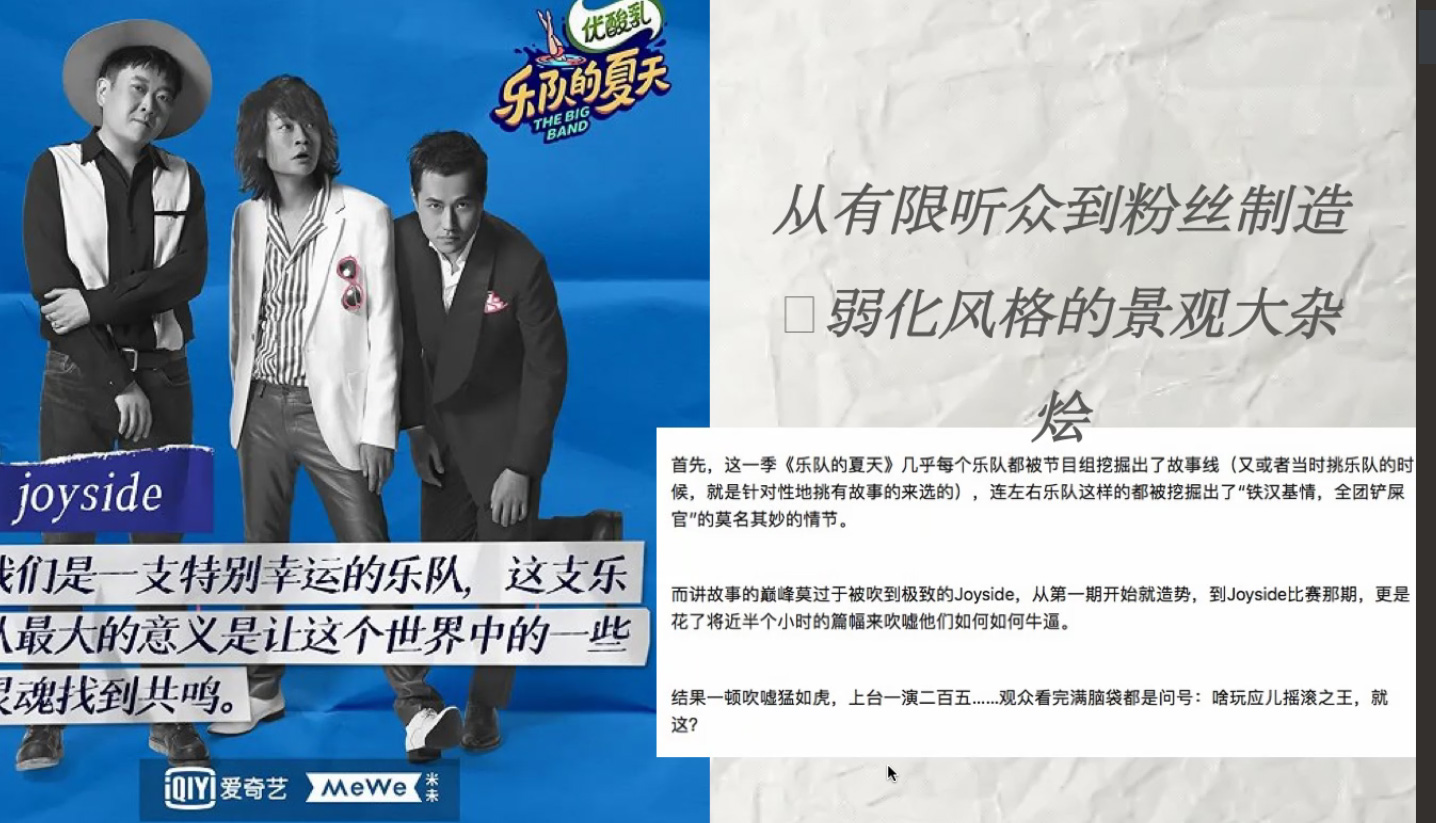
演讲中提到的乐队与节目的相关信息
正如我在PPT中分享的那样,在这个节目里的每一支乐队几乎都被学生们录制下来,来研究它的故事线。也不论乐队的倾向是偏左还是偏右,他们诸如使命与理想,青年人的热血和激情,消费主义与对职场的情感等等故事元素都得到了传播。这里我举一个中国著名的老牌朋克乐队Joyside的例子,在节目里的首次亮相中,他们花了差不多半小时的时间来回溯乐队成立和发展过程,以展示傲人的历史。
总之,整个节目的编排、剪辑都是围绕着上面的主题展开。他们诉说的有关亚文化色彩的故事确实会变的富有创意、有意思和产生共鸣,但有时可能会丧失独特性,将“脱离主流”的元素进行包装。 所以我想用我一位同事在评述《中国有嘻哈》时说的话来结束我的谈话,那就是《乐队的夏天》与《中国有嘻哈》的场景建构有相同之处。
在这句话中,她说在西方语境中嘻哈音乐与其他领域的产品有着严格的界限,而在中国大规模产业增长的情况下,这个边界却越来越模糊。但不可否认的是,正是《中国有嘻哈》将嘻哈音乐创作的产品形态官方地划定出来,亚文化也是得到主流的赋权而得以发展,它在风格杂糅了民族文化的传承与现代时尚的元素。在这个赋权过程中,亚文化的颠覆性的要素是存在的,然而中国的嘻哈音乐赋权更多是政策而非市场力量驱动。在这个过程中新的创作者和阐释会涌现出来,因为这是“准备好了的”亚文化场景,是既定存在的。然而,这些要素仍然更多的是非市场发展的结果。
肖剑,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艺术与媒介(AMF)国际论坛总策划,艺术与英国拉夫堡大学媒介与文化分析博士,兼任墨尔本大学公共文化中心研究员,青云文社研究所学术主持;原英国《Nottingham Evening Post》记者,《Mind》记者,英国“New Art Exchange” 美术馆策展人,并参与策划多项国内展览。
主要研究领域为城市美学与传播、公共艺术介入、媒介与文化分析等。出版英文专著《Punk Culture in Contemporary China》,中文专著《影像-城市-历史:1891年以来深圳的变迁与重塑》(即将出版)。发表在中英文期刊上的研究成果已有二十余篇,集中在文化研究(如《European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传播学(如《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城市研究(如《Journal of Urban Affairs》)、流行音乐研究(如《Journal of Popular Music Studies》)等方向,并与国内外学者共同完成创意城市著作、区域文化著作等。主持并参与多项相关科研项目,并担任《Journalism Practice》、《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City、Culture and Society》等期刊评审。以下内容为肖剑在分论坛“地下、实验与声音”上的发言内容与其关于“艺术世界”内容的相关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