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交叉滚子隔离块(官方)官方网站
——
交叉滚子隔离块(官方)官方网站,注册资金为人民币1000万元,是一家集现代化专业研发、生产、制造、汽车零部件、轴承的企业。公司坐落于十三朝古都洛阳,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捷。我公司是集研发与生产为一体的企业,拥有自己的工厂,经营范围主要包括:轴承及汽车零部件、轴承隔离块、轴承保持器、风电轴承集油瓶、YRT保持器、工程塑胶件的研发、生产、制造与销售的企业。公司拥有自己的研发团队及精良的全自动化生产设备,专用检测实验室和精密检测设备,各种设备齐全...
常规型号产品48小时内发货,坚持诚信经营
我们提供一系列定制加工服务

公司内部的工程师拥有专业的技术知识
YRT轴承保持器
YRT bearing retainer
洛阳维尚轴承所生产的YRT保持器型号包括50、80、100、120、150、180、200、260,支持型号定制、量大从优
咨询电话:13653794806
精密检测设备
Precision testing equipment
——
公司拥有自己的研发团队及精良的全自动化生产设备,专用检测实验室和精密检测设备,各种设备齐全


新闻中心
News Center
——
维尚优势
Weishang Advantage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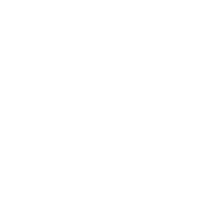
精英团队
公司员工近200人,研发团队近20人,年销售额5000多万,具备丰富的产品加工制造的经验与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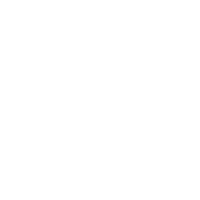
产品支持定制
公司集研发与生产为一体,拥有自己的工厂,所生产的交叉滚子隔离块、轴承保持器、风电轴承集油瓶、YRT保持器等产品可根据客户需求进行定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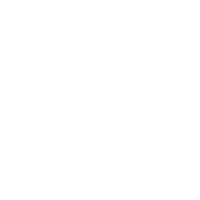
服务市场
遍布全国各地的销售网络为客户提供便捷优质的售前售后服务
© 2021 交叉滚子隔离块(官方)官方网站 豫ICP备2021003538号 网站建设:中企动力 洛阳

豫公网安备 4103050200044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