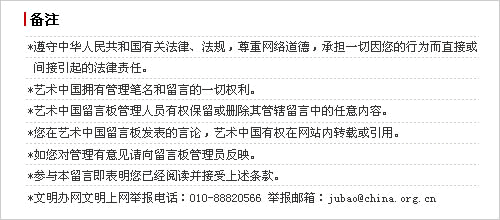少年时期与马列
蔡国强这一代的中国人有个特色,他们从小学马列思想,长大之后又以马列的辩证方法反思中国体制与社会的问题。相较之下,他便体会到自己的父亲与父执辈那批文人,在对中国社会变化的看法上,存在的明显冲突。
跟蔡国强同辈的中国艺术家常常拿少年时期经历的某个时期,化作日后艺术创作上的重要养分,相对地,蔡国强的作品中比较少看到那个特定时期的直接影响。不是真的没影响,而是以一种幽微、细腻的方式呈现影响,不直接拿那个特定当成创作主题和作品素材。
蔡国强在泉州长大,相较于其他都市,泉州在那个特定时期中受到的伤害是比较小的。不过他仍然记得,只要毛主席的最高指示一出来,就算是半夜大家也要敲锣打鼓上街游行。
“这就像是一场行为艺术,是我生命中最早体验到的仪式感。”
他记得,大伙儿上街敲锣打鼓宣扬毛泽东的最新指示,游行之中每个人都可以走在马路中央,没有任何红绿灯讯号。大家在街上吶喊,发出很大的声音,有时还高声唱歌。想想平时只能走在马路边,游行时却可以走到路中央,还有好多人看着,那种感觉很棒。少年们还会半夜拿小凳子到体育场,听取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天亮后继续上街敲锣打鼓。
“那段时间中国的生产力很差,但是南方相对来说没那么严重,虽然吃得也不好,但小孩子对吃没有太多感觉。”
泉州的文人气息浓厚,保留了许多传统。不少人整天在画菊花、画兰花,他们坐在一起感慨中国文明的伟大,或是赞叹过去中国五千年的辉煌历史。蔡国强的父亲及他交往的朋友就是这样的人。即便在那个特定时期,以及经历那个特定时期之后,仍然紧守着某种既定的思考与生活感。
他说,对文人来说,当然那个特定时期不可能完全不带来生活上的影响。像是因为“破四旧”,就必须把一些书藏到乡下去。像是因为那个特定时期的关系,不能照平常画黑白的水墨,必须加了彩,改画红色的花。什么样的红花呢?本来画兰花的,现在要改画鸡冠花。
当时蔡国强在学校中受到毛泽东思想、马列主义的熏陶,一直到现在都还没有忘掉。在国际艺坛发展,“不破不立”、“制造议论”、“建立根据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些简单的共产党思想和口号,会在一些奇特的地方给他启发。
就是因为这些思想训练的基础,蔡国强理解到群众与人民的重要性。
“毛泽东当初提出:中国的问题有千条万条,最根本的是土地问题。当国民党铆足劲地想搞现代化城市建设的时候,毛泽东却深刻地认识到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于土地。处在半封建与半殖民的中国,广大的穷苦乡村人民渴望拥有自己的土地,他们希望不被地主剥削,那种翻身做主人的强烈要求,便是共产党夺天下的基础。”
蔡国强也从马克思主义学到,“世间有无数的矛盾,在各种矛盾之间,只有一个矛盾是主要的,其他矛盾是次要的。先解决主要矛盾,次要矛盾就容易迎刃而解。但是次要矛盾如果不小心,也会慢慢升华成为主要矛盾。另外,每一个主矛盾中又有矛盾的主要与次要方面。”
这些知识与辩证思考都是蔡国强从小被培育出来的。马克思的辩证法建立在黑格尔等西方哲学基础之上,所以日后蔡国强在欧美作展览时,跟西方人讨论彼此见解,很容易进入对话的状态。相较之下,他觉得自己刚离开中国到日本居住时,尽管日本人很喜欢蔡国强,也能欣赏他的作品,但是跟日本人对话就比较麻烦,因为基本上蔡国强讨论思考是辩证法的概念,日本人比较没有这样的习惯。
从小学、中学到大学,蔡国强的学习表现一贯很优秀,所有老师都欣赏他,包含政治经济学这类困难的科目,他都能拿到很高的分数。但随着年纪愈来愈大,将少年时期所学的那些知识,反映在中国的政治问题仔细审视的时候,蔡国强开始有了不同的想法。他开始觉得那套思想不太对劲。
“比方说,一个国家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要相适应,才不会让生产关系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但当时的体制系统明明白白地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蔡国强在很年轻的时候,就会用马列主义来反思当下的社会问题,反思中国的矛盾。“中国教了我们马列这套哲学为基础,而我又用这武器批判了它。”
蔡国强这一世代的中国人有项特色,他们从小学马列思想,长大之后又以马列的辩证反思中国体制与社会的问题。相较之下,他便体会到自己的父亲与父执辈那批文人,在对中国社会变化的看法上,存在的明显冲突。
“我父亲那一辈的文人尝过旧社会的苦,所以他们对新社会带来的问题,态度比较宽容,总是会说好话,或者是帮这些痛苦找理由。就这个角度来说,父执辈还比我们年轻的这一辈更支持新社会的,有趣的是,他们一方面拥抱新社会,另一方面又怀念过去传统的文人文化,我跟我父亲常为此争论。”
蔡国强总是质疑父亲怎么可以永远活在民族过去的荣光与幻觉中?
蔡国强年轻时,看到香港人带进大陆那些印刷精美的挂历,图片上呈现出香港繁华的高楼大厦。他告诉父亲,光是这个照片挂历展现的模样,就可以明白中国的经济建设根本是停滞的,
但蔡国强的父亲会说:“这有什么了不起?宋代的时候中国就已经盖出很高的宝塔了!”父亲以千年前中国的伟大成就作为今日的荣光基础,拿的都是过去的全盛时期做例子。
因此,现在回头想想,他的人生,出国是真正的转折点。
“像我这样的人要是留在国内,肯定既当不了艺术家,也当不了改革派。因为我不愿意、也没有胆量去对抗政权。”他是那种绝顶聪明又认定人生必须可以睡懒觉、自由自在的人。他也不是那种会花时间与人争论观点的人,常常觉得谁对谁错都没关系。
这样的心态,怎么可能留在中国成为改革派?
“我知道在中国有人对民族的命运感到痛苦着急,想要积极改革,想要提高人民福祉与社会发展,非得要把自己的鲜血奉献给这块土地。我对这种伟大目标的感受不强烈。但是我却也没有足够的条件能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当个自由化的个体户,去搞现代艺术。”
蔡国强跟着自己的感觉走。没上大学,还在泉州剧团搞舞美画布景的时候,心中就暗暗作出要离开这块土地的打算。之后他到上海读书,也默默地持续作着这样的准备。
也许是因为很早就知道自己会离开家乡的关系,在家乡的时候,蔡国强很珍惜家乡的山水,对家乡的一切格外眷恋。读大学的时候,每一个暑假他都拿着自己工作存下来的钱,加上母亲为他存好的结婚用款,到处去旅行,想趁自己还在中国的时候,走遍中国的每一个地方,好好地认识中国。当时同学间不时兴旅行的,因为对风景山水的歌咏,正是他们要革命批判的对象,在当时也很不前卫。蔡国强不管他们,自己跟女友去看敦煌,去看青藏高原、丝绸之路、苏州园林、火焰山等等,把中国走过一遍,好好地将这些景象记下。
“现在回想起来,我心里似乎有分紧迫感,感受到自己就要离开这块土地了,即将与中国文化有一段漫长的分离。”
他很清楚,继续留在这块土地上,会一直向往西方以及西方所代表的那个先进的世界,一心只想追求西方文明,动不动就想着美国的观念艺术或是抽象艺术,老想着安迪?沃霍尔这些艺术家会怎样做艺术,脑子只会向往那个他觉得很了不起的社会。
“然后我会变成一株很可怜、没有生长基础的盆栽。”
“就算在中国我真的成了艺术家,我也每天只渴望知道国外的西方艺术家到底在做什么创作,变成一个找不到自己脉络的可悲艺术家。”
“这对我来说是非常可怕的,若我留在大陆,我觉得我会妥协的。”
他知道自己会离开。
蔡国强还记得泉州的青山绿水。早晨起来他光着上身跑步,家一出去是环城路,环城底下是环城河,河的那边就是农村。他跑步的时候妈妈在河上洗衣服。那个特定时期这座宋代建造的泉州城墙被拆了,各个大小城门都拆掉了。跑步的时候会看到河的对面,一二十米宽,河那边一岸的油菜花田上铺着一层紫紫的雾气,阳光变大后,那雾气才慢慢褪开来。
那时候他就知道,自己会离开这里,离开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