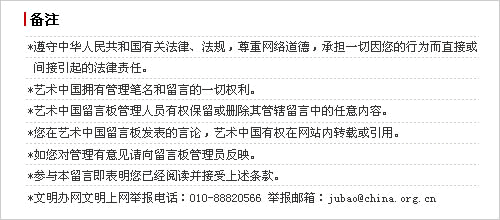“我有些哲学价值作为基础,才敢一下子做这个、另一下子做那个。我是建立在我的信心上,要相信这套哲学是有价值的,相信它对世界的观察是正确的,就可以去掌握万变的艺术家生涯。”
火药、装置、行为、观念艺术,这是博物馆或是美术研究上对于蔡国强作品的分类方式,或者是用博物馆展览方式的分类也很多,像是装置艺术、爆破计划、火药草图,这样的分类法,简单清楚,方便观众参观理解。
但是蔡国强对自己的作品有一种独特的分类方式,这种分类方式比较以他的创作概念出发,像是他跟自己的对话一样。
“我知道一般博物馆对我作品的分类是有道理的,那是西方式的,有博物馆服务公众的精神,这样做观众比较好理解。”不过,蔡国强自己的分类法是:“我将自己的作品分成视觉性的、诗意的、诗的视觉世界化等等,我知道如果用我的分类法,一定更让人难懂。”
“有的时候我将作品以生、死来区分,有的作品的概念则是药、治愈,这些是对生的关怀和向往,而像焰火的作品,就算是奥运会的盛大焰火 我都将它们分到死的类别,它们都在瞬间中消灭了自己,华丽圣诞一瞬消失,你可说它们赢得了永恒的追求。”
“不过,这些分类法都没有用,我自己好玩罢了。”
他还有其他的分类方式。“我有一种是姿态性的,还有一种是对历史的 不是守旧,就是很喜欢与历史缠绵在一起。类似怀旧但又不是,就是我经常一直做美术史,把美术史拿来做成作品。”
“我总是在自己的历史中拿东西,几个资源不断地开发,像是泉州的资源:如帆船、中药、风水和灯笼。故乡是我的仓库。”
不过,不管是生或死,药或治愈,姿态或历史,这么多不同分类法中,蔡国强这些出自不同创作灵感与不同形式的作品,有一个共同的核心:“百花缭乱,推新出陈。”
这个推新出陈就是推陈出新的相反。这个陈,就是作品里头一以贯之的东西,也是他在艺术上追求的终极目标,就是他的“道”:“什么都可以变,唯有道不变。”
这个“道”像是《易经》提到的一样:“什么都可以变,唯一不变的是可变的规律。『变』是不可变的。万物皆变,唯有变不可变。”
“我以这些哲学价值作为基础,才放心一下子做这个、另一下子做那个。我是建立在对这些的信心上,要相信这套哲学有价值的,要相信它对世界的认识是基本正确的,就可以用这些哲学去掌握万变的艺术家生涯。”
“我们是有限的人,生活模式、文化背景、所处的世代等,都是有轨迹的,这个轨迹刚开始不要用一个不变的目标去主张,就把自己打开,放下身段,自由自在地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但你不要以为别人看不出你的门道。三下两下你的基本规律就被看出来了,但是这个规律不是自己去追求的,是万变不离这个规律。”
“所以,规律不是建立在寻找,而是建立在信心。有信心就会有规律,因为你用的这套哲学是自己有信心的。”
如果要蔡国强以生命经验以时期来分,可以分成“中国时期”、“日本时期”、“美国时期”及最近的“春秋战国时期”。“之所以称为春秋战国时期,是因为我做的事情更多元了,这个时期又包含了我回到中国做的事情。”
而“美国时期”与“春秋战国时期”的分期点,在于蔡国强放弃了他经典的《为外星人所作的计划》。
“因为这件事情已经变得不单纯了。”蔡国强在日本开始创作“外星人”系列,出自他当时的思考与环境,外星人系列作品的精神层次上是人渴望与无限的东西对话的强烈欲望,所使用的材质不是高科技,而是传统的、能量的、大地艺术般的爆破。做外星人计划还有另一个原因,是因为在日本的时候,物理空间非常狭小,文化上不管怎样思考现代艺术,西方似乎是你的对立面,当时日本考虑的问题大量是东西方问题,所以蔡国强想要找一个超越东西方的格局,于是想到宇宙,想到人与外星人之间的关系,所以在日本会想要做这个计划。到了美国之后,很多主题都针对社会、政治发言,很多活动的预算或规模开始变得庞大,动辄几十万几百万美金。要不然就是受邀去做开幕式。“我已经不能假惺惺地把它做成外星人计划,因为基础已经没有了。”
“我和做作品的关系有点像是在 自慰,自己玩兴奋点、临界点、紧张关系。”
艺术家最要坚持的一点是“诚恳”。“最重要的是真诚:真做作品,真正思考问题,真正在发现自己的可能性,真正焦虑,真诚的感受人、生命和爱情。”
“对于自己的改变要有信心,艺术家不可能永远做着同样的事情。依赖就做不好作品了。包括对火药我也没有依赖,而是对精神、瞬间、暴力、危险、偶然、不可控制性感兴趣,对颠覆自己感兴趣。当我想要做爆破,又想成为一个好的画家,这两者的矛盾便开始出现。从童年到大学的受教育过程,我的理想是成为画家,是保持美术史描述的那种艺术家,可是我现在做的是狼、是老虎等等装置艺术,会有一股不安,觉得自己不是画家,于是我保持做草图爆炸,在平面上经营童年的画家梦。”
“我安心地在这个状态中开拓着,但三下两下几年后连奥运的《大脚印》我都已经做出草图来。”
“若我还是坚持火药是只能在外面做的爆炸,我也会枯萎。”
他又决定要让自己面对新的课题,迎接新的挑战与可能。比方在台湾举办回顾展,他决定进行新的作品,包括太鲁阁山水和《昼夜》的人体描绘,“就是想回到绘画本身,迎接绘画本身的挑战”。从古希腊、古罗马到印象派,人体在西方已经做到极致了,到了现代艺术之后,这主题就连在西方都不容易,况且要用火药这种暴力性的材料,去表现这种纤细的美。
“我有印象派时代的情结:夕阳下对着风景,边画画边唱歌,一切都在里面了。”
“当我一直做外星人系列,一直在大地、在外面世界做爆炸,这领域里人家不好跟我比,因为太特殊了,我很容易建立自己存在的理由。但当我在这块领域已经塑造出风格的时候,我还需要进一步面对的难题 回到绘画本身去挑战。”
“因为时代不同了,绘画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被不同时代的精英们不断地努力探索过,留给我们的空间所剩无几。此时此刻,选择绘画作为人生目标的人,是需要有非常的勇气与胆量的。不清醒的话,就是自得其乐了,那也是很美好的。”
蔡国强探索绘画的方式也是以火药进行。他试图从爆炸平面草图去进行他对绘画的探索与变革。“草图是在纸上画爆炸,赢得画画的感情,让我觉得我还在平面上做事。”
“我希望我的纸上爆破草图,最终的呈现,可以用绘画性的一切来检验,它是不是好绘画。也就是说,这件作品在二维空间所面临的浓淡、韵律、构图、色彩、动静等等美学上的感受,是不是够强?并且,更进一步,我希望要求,作为一种绘画艺术,它有没有探索出新的东西 所以,最终还是要回到美术本身来解决自己的困境。”
“我留恋爆炸草图平面的美学,还有,它可以是使我自己对话,也是自慰、前戏、爆炸、高潮的完成,而这一切是很个人的,不需要大型爆破计划那样社会运动式的。”
从中国、日本到美国到全世界,从大地的爆破、装置艺术、观念艺术,到此火药来解决绘画的问题。蔡国强一直在变,以万变应他的不变。
“我与未来的关系是非常不牢固的,我也怕它是牢固的。”
“我曾想过,如果今天我不是艺术家,可能是战乱时代的军阀,带兵打仗。在日本我就曾开玩笑说,若不是在这个时代,我们可能是在战场上彼此打仗的。”
他说,不过在和平时代很好,男孩子可以把自己的理想与能量,都投入不会造成人类不幸的事物。
我现在就只觉得做艺术是好玩的,其他事情我都做不来,而且要做别的事情也太晚了。”
他想了想又补上一句:“其实一定不会吗?这种事情我真是不知道。”
“艺术家除了要对自己坦承,艺术家最后的乐趣,都是要回归到有没有诚实面对艺术本身的问题。艺术在开始的时候应该要离开艺术,但最后仍要以艺术为归结。”